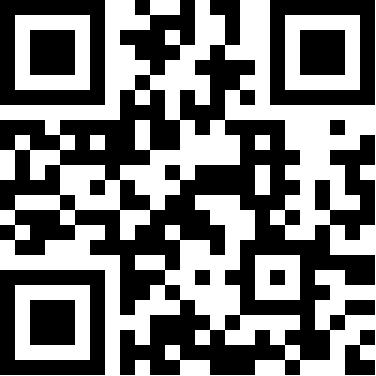小儿变蒸说有关资料|生命科学(田合禄)
- 索引:519
- 发布时间:2019-06-24
- 点击次数:
- 加入收藏
- 发表评论
- 语音阅读
小儿变蒸说有关资料|生命科学(田合禄)

http://www.daode99.com/view.php?tid=1092
2013-09-18 来源:网络 阅读: 10356次
小儿变蒸说有关资料|生命科学[页1]
小儿变蒸说有关资料
田合禄 /文
一、王叔和最早提出变蒸说
小儿变蒸说是晋代王叔和最早提出来的,他在《脉经·平小儿杂病证第九》中说:“小儿是其日数,应变蒸之时,身热而脉乱,汗不出,不欲食,食则吐哯者,脉乱无苦也。”认为小儿变蒸是一种生理现象。
二、变蒸的定义
对于变蒸的含义,历代医家有不同的解释。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变蒸候》认为:“小儿变蒸者,以长血气也。变者上气,蒸者体热。”
唐代孙思邈《千金方·变蒸论》说:“小儿所以变蒸者,是荣其血脉,改其五脏,故一变竟,辄觉情态有异。”
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变蒸》则对变蒸作了进一步详细解释:“小儿在母腹中乃生骨气,五脏六腑成而未全。自生之后,即长骨脉、五脏六腑之神智也。变者,易也,又生变蒸者,自内而外,自下而上,又身热,故以生之日后三十二日一变。变每毕,即有情性有异于前,何者? 长生脏腑智意故也。”
元代朱丹溪《幼科全书·变蒸》认为:“此小儿正病者,盖变者易也,每变毕即情性有异性于前,何者?生长脏腑之智意也。蒸者,蒸蒸然热也。万物生于春,长于夏者,以阳主生长也。于人亦然。所以变蒸足始乃成人,血气充实、骨肉坚牢也。小儿此证如蚕之有眠,龙之脱骨,虎之转爪,而变化同也。”
明代万全《幼科发挥·变蒸》云:“变蒸非病也,乃儿生长之次第也。儿生之后,凡三十二日一变,变则发热、昏睡不乳,似病非病也。恐人不知,误疑为热而汗下之,诛罚太过,名曰大惑。或误以变蒸得于胎病者。或曰:儿之生也,初无变蒸,既生之后,当以三十二日一变,至于三百八十四日之后,又无变者,何也? 曰:初无变蒸者,藏诸用,阴之合也;中有变者,显诸仁,阳之辟也;终无变者,阴阳合辟之机成也,故不复蒸也。故儿之初生,语其皮肉则未实也,语其筋骨则未坚也,语其肠胃则谷气未充也,语其神智则未开发也,只是一块血肉耳。至于三百八十四日,然后脏腑气足,经络脉满,谷肉果菜,以渐而食,方成人也。”
明代徐春圃《古今医统·变蒸》云:“初生小儿变蒸者,阴阳水火变蒸于气血,而使形体成就,是五脏之变而七情所由生也。变者性情变易也,蒸者身体蒸热也。”
明代李梃《医学入门·变蒸》云:“小儿初生,形体虽具,脏腑气血尚未成就,而精神志意魂魄俱未生全。故变蒸既毕,学语倚立,扶步能食,血脉筋骨皆牢。禀气盛者,暗合而无外证,禀气弱者,乃有蒸病。”
宋代无名氏《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概括前人对变蒸的含义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小儿在母腹中,胎化十月而生,则皮肤筋骨脏腑气血,虽已全具而未充备,故有变蒸者,是长神智、坚骨脉也。变者易也,蒸者热也。每经一次之后,则儿骨脉气血稍强,精神情性特异。是以《圣济经》言:婴孺始生有变蒸者,以体具未充,精神未壮,尚资阴阳之气,水火之济,甄陶以成,非道之自然以变为常者域? 故儿自生每三十二是一次者,以人两手十指,每指三节,共骨三十段,又两掌骨,共三十二段以应之也。足亦如之。太仓公曰:气入内支,长筋骨于十变者,乃是也。《圣济经》又曰:变者上气,蒸者体热。上气者,则以五脏改易而皆上输,藏真高于肺也。体热者,则以血脉敷荣,阳方外固为阴使也。故变蒸毕而形气成就者也,亦犹万物之生,非阴阳气蕴热蒸无以荣变也。”
清代夏禹铸在《幼科铁镜·辨蒸变》中说:“小儿生下三十二日一变,六十四日一蒸。变者,变生五脏;蒸者,蒸养六腑,长血气而生精神、益智慧也。”也就是“变者,变其情智,发其聪明;蒸者,蒸其血脉,长其百骸。”即指小儿变蒸是小儿形体发育(生脏腑、长血脉百骸)和精神发育(变其情智、发其聪明,声音、笑貌、举止、灵敏皆进一步)的生理现象。
三、变蒸时日与变生脏腑
对于小儿变蒸的时间日期,比较一致的见解是生后每32日一变,64日一蒸,共十变五蒸,后又三大蒸(即64日第一大蒸、再64日第二大蒸、再128日第三大蒸)毕,则变蒸全部完成。
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又载另一法,为九变四蒸,计288日。《颅囟经》则认为每30日一变,60日一蒸。明万全《幼科发挥》把十蒸改为十二蒸,共384日变蒸毕。还有45日、49日、60日为一周期的(《冯氏锦囊秘录》、《幼幼新书》、《颅卤经》)。都与八卦历法周期有关。
这与现代医学观察小儿生长发育过程按1月及智力按33天来算,与32日基本一致。至明方贤《奇效良方》则说:“若及三十齿者,变蒸足也。”把变蒸的时间范围延到智齿萌生时,即20—30岁了,这一说法太离谱了。
另外,不少医家认为多不依法而变,这是没有临床实践基础的人的说法。也有人认为有暗变者。
对于以32日为变蒸的周期,至少有5种解释:
1、钱乙以周天365度,应人身365骨,除手足45碎骨,余320骨,人一日长10骨,32日后320骨均长一次。
2、《小儿卫生总微论》以人两手十指及掌骨共32骨节应之。
3、方贤《奇效良方》以人32齿应之。
4、万全以五脏六腑、十二经络以应64卦爻,其中六腑配阳卦32,五脏配阴卦32。
5、赵佶《圣济经》因肝应生长之气,而肝数八,八得四而治,四八得32日为一次变化。
我们要择善而从。
至于变生脏腑,是指体形大小的生长发育,不是指生出。出智慧,则是指精神上的生长发育。变生脏腑说是符合实际的。但自古以来,变生脏腑的先后顺序说法不一,也有不少医家如明代张景岳、清代陈复正等对此持否定态度。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变蒸候》云:“其变日数,从初生至三十二日,一变;六十四日再变,变且蒸;九十六日三变,……至一百二十八日四变,变且蒸:一百六十日五变;一百九十二日六变,变且蒸;二百二十四日七变;二百五十六日八变,变且蒸;二百八十八日九变;三百二十日十变,变且蒸。积三百二十日小蒸毕,后六十四日大蒸,后百二十八日复蒸,积五百七十六日,大小蒸毕也。”
唐代孙思邈《千金方·少小婴孺方》记载的变蒸时日与《诸病源候论》相同。但该篇中又记载一法,仅至九变四蒸,即二百八十八日。其云:“又一法,凡儿生三十二日始变,变者身热也;至六十四日再变,变且蒸,其状卧端正也;至九十六日三变,变者候丹孔出而泄;至一百二十八日四变,变且蒸,以能咳笑也;至一百六十日五变,以成机关也;至一百九十二日六变,变且蒸,五机成也;至二百二十四日七变,以能匍匐也:至二百五十六日八变,变且蒸,以知欲学语也;至二百八十八日九变,以亭亭然也。凡小儿生至二百八十八日,九变四蒸也。”
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变蒸》对变生脏腑、长骨添精神作了详细论述:“何谓三十二日长骨添精神?人有三百六十五骨,除手足中四十五碎骨外,有三百二十数。自生下,骨一日十段而上之,十日百段,三十二日计三百二十段,为一遍,亦曰一蒸。骨之余气,自脑分入龈中,作三十二齿。而齿牙有不及三十二数者,由变不足其常也。或二十八即至,长二十八齿,已下仿此,但不过三十二之数也。凡一周遍,及发虚热,诸病如是,十周则小蒸毕也,计三百二十日生骨气,乃全而未壮也。故初三十二日一变,生,肾生志:六十四日再变,生膀胱,其发耳与尻冷。肾与膀胱俱主水,水数一,故先变。生之九十六日三变,生心喜;一百二十八日四变,生小肠,其发汗出而微惊。心为火,火数二。一百六十日五变,生肝哭;一百九十二日六变,生胆,其发目不开而赤。肝主木,木数三。二百二十日七变,生肺声;二百五十六日八变,生大肠,其发肤热而汗或不汗。肺属金,金数四。二百八十八日九变,生脾智;三百二十日十变,生胃,其发不食、腹痛而吐乳。此后乃齿生,能言知喜怒,故云始全也。太仓云:气入四肢,长碎骨于十变,后六十四日长其经脉,手足受血,故手能持物,足能行立也。经云:变且蒸,谓蒸毕而足一岁之日也。……足以小儿须变蒸,脱齿者如花之易苗。所谓不及三十二齿,由变之不及。齿当与变日相合也,年壮而视齿方明。”
宋代刘昉《幼幼新书·卷七》对变蒸变生脏腑顺序提出不同观点:“一蒸肝生魂,肝为尚书,蒸后魂定令目瞳子光明;二蒸肺生魄,肺为丞相,上通于鼻,蒸后能令嚏嗽;三蒸心生神,心为帝王,通于舌,蒸后令儿能语笑;四蒸脾生智,脾为大夫,藏智,蒸后令儿举动任意;五蒸肾生精志,肾为列女,外应耳,蒸后儿骨髓气通流;六蒸筋脉伸,蒸后筋脉通行,九窍津液转流,儿能立;七蒸骨神定,气力渐加,蒸后儿能举脚行;八蒸呼吸无停息,以正一万三千五百息也,呼出心肺,吸入肾与肝,故令儿呼吸有数,血脉流通五十周也。”以上八蒸,即十变中的五小蒸,复十变后的三大蒸。
明代万全在《幼科发挥·变蒸》中提出12变合384日的变蒸时日,变生脏腑也与钱乙所论稍有不同,是按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来相配的。他说:“变蒸之日必以三十二日者,何也? 曰:《易传》云:生生之谓易,易者变易也。不变不易,不足以见天地生物之心。人有五脏六腑,以配手足十二经络。腑属阳,以配阳卦三十二;脏届阴,以配阴卦三十二。取其一脏一腑,各以三十二日一小变,六十四日一大变。阳卦之爻一百九十二,阴卦之爻一百九十二,合岁并闰月凡三百八十四爻。所以变蒸一期之日,三百八十四,以应六十四卦爻之数也。或曰:三十二日一小变,六十四日一大变,所生者何物也? 所生之物亦有说欤? 曰:形既生矣,复何生也。所生者,五脏之知觉运动也。故初生三十二一变,生足少阴肾癸水,肾之精也;六十四日二变,生足太阳膀胱壬水,而肾与膀胱一脏一腑之气成矣。此天一生水也,水之精为瞳子,此后始能认人矣。九十六日三变,生手少阴心丁火;一百二十八日四变,生手太阳小肠丙火,而心与小肠一脏一腑之气足矣。此地二生火也,火之精为神,此后能嬉笑也。一百六十日五变,生足厥阴肝乙木;一百九十二日六变,生足少阳胆甲木,而肝与胆一脏一腑受气足而神合矣。此天三生木也,木之精为筋,此后能坐矣。二百二十四日七变。生手太阴肺辛金;二百五十八日八变,生手阳明大肠庚金,而肺与大肠一脏一腑之气足矣。此地四生金也,金之精为声,此后始能习人语矣。二百八十八日九变,生足太阴脾已土;三百二十二日十变,生足阳明胃戊土,乃脾胃一脏一腑之气足矣。此天五生土也,土之精为肉,脾胃主四肢,此后能匍匐矣。三百五十二日十一变,生手厥阴心包络;三百八十四日十二变,生手少阳三焦,三焦配肾,肾主骨髓,自此能坐能立能行矣。变蒸已足,形神俱全矣。……凡一变之时,则筋骨手足以渐而坚,知觉运动以渐而发,日异而月不同。”
明代徐春圃《古今医统大全·变蒸》则对钱乙论与刘昉所引有了新的认识,认为“二说俱通”,但“亦有不依序而变,如伤寒不循经之次第也。”
对变蒸依期而变生脏腑持否定态度的代表人物有明代张景岳、清代陈复正、任赞,以及民国时期的奚瓒黄。
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小儿则》中云:“小儿变蒸之说,古所无也。至西晋王叔和始一言之,继隋唐巢氏以来,则日相传演,其说益繁。然以余观之,则似有未必然者。何也? 盖儿胎月足离怀,气质虽未成实,而脏腑亦已完备,及既生之后,凡长养之机,则如月如苗,一息不容有间,百骸齐到,自当时异而日不同。岂复有此先彼后,如一变生肾,二变生膀胱,及每变必三十二日之理乎?又如小儿之病与不病,余所见所治者,盖亦不少,凡属违和,则不因外感,必以内伤,初未闻有无因而病者,岂真变蒸之谓耶! 又见保护得宜,而自生至长,毫无疾痛者不少,抑又何也? 虽有暗变之说,终亦不能信然!”
清代陈复正《幼幼集成·变蒸辨》也说:“小儿脏腑骨度,生来已定,毫不可以移易者,则变蒸应有定理。今则各逞己见,各为臆说,然则脏腑竟可以倒置,骨度亦可以更张? 是非真伪,从何究诘?谓天一生水者为是,则木火相生、木金相克者非矣。谓木火相生、木金相克者为是,则天一生水者非矣。徒滋葛藤,迄无定论,将使来学,何所适从? 所幸变蒸非病,可任其颠倒错乱。假使变蒸为病,率宜依经用药者,岂不以脾病而治肾,膀胱病而治胃乎? 总之,此等固执之言,不可为训。盖天地阴阳之理数,可限而不可限,如五运六气为一定不易之规,而有应至不至,不应至而至,往来胜复,主客加临,有应不应之殊。天地尚且如斯,而况婴儿之生,风土不侔,赋禀各异,时令有差,膏藜非一,而以此等定局,以限其某时应变,某时应蒸,予临证四十余载,从未见一儿依期作热而变者。有自生至长,未尝一热者,有生下十朝半月而常多作热者,岂变蒸之谓乎? 凡小儿作热,总无一定,不必拘泥,后贤毋执以为实,而以正病作变蒸,迁延时日,误事不小。但依证治疗,自可生全。”[9]
清代任赞《保赤新编·卷上》则提出四点不解之处:“人既成形以生,气血渐长,日异而月不同,本享通利遂, 自然之理,岂必烧热而后变乎?不可解者一也。三十二一变之期,不过约略会计,非三十二日以前尚未变,三十二日以后复止不变也? 变既有热,自应无时不热,何以偏临此数日间而始见耶?不可解者二也。儿之初生,脏腑形骸已具,所少者神智耳。据五行生成精理,是变生脏腑之神智,非直生脏腑也。又何以按心包络三焦两经为无形状而曰不变不蒸? 且谓长碎骨于十变后,更有三大变乎? 不可解者三也。有则为明变,无则为暗变,其说已属渐移,况虚弱不耐风寒之儿,身热常见者有之,岂他时俱属邪病,而此数日独为正病乎?抑所辨者全在唇内白泡及耳尻冷乎? 不可解者四也。”
近代奚瓒黄所著《小儿病自疗法》对变蒸日期亦予以否定,但对生长发育表现出的气质变化现象,却是赞同的。他说:“变蒸之期不可信,而气质变化之微必有因。比如四时代谢,四时必有寒热温凉、风雨晦螟之变纪,而小儿之气质变化,神情上岂无一种现象? 其乍寒乍热、精神不畅,或不乳吐口见等证,皆是气质变化表露于精神上之现象也。”
在整个变蒸过程中,小儿的生长发育是连贯的,从一变到大小蒸毕,“一息不容有间”。但各阶段的生长发育速度不尽相同,各有特点。从出生到1岁的婴儿期生长发育速度最快,1岁到3岁的幼儿期随着年龄增长生长发育相对减慢,符合小儿的生长发育规律。故将变蒸576日之期分为十变、五小蒸、三大蒸等阶段,且每阶段间隔时间逐渐延长。如在320日内经历十变五小蒸,每变32日,每蒸64日,320日后历两大蒸,每蒸64日,再历一大蒸128日。
四、变蒸的临床表现与治疗
对变蒸的临床表现一般认为轻重不同,也有认为无临床表现者为暗变。变蒸的临床表现一般出现在变蒸期交换的前后数日。因变蒸是小儿生长发育的正常生理现象,属正病而非邪病,一般无需治疗,但症状较重或有兼证者则需用药治疗。兹引录具有代表性的几位医家论述予以说明。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变蒸候》云:“变者上气,蒸者体热。变蒸有轻重。其轻者,体热而微惊,耳冷尻亦冷,上唇头白泡起,如死鱼目珠子,微汗出,而近者五日而歇,远者八九日乃歇;其重者,体壮热而脉乱,或汗或不汗,不欲食,食辄吐观,无所苦也。变蒸之时,目白睛微赤,黑睛微白,亦无所苦,蒸毕自明了矣。先蒸五日,后蒸五日,为十日之中热乃除。变蒸之时不欲惊动,勿令旁边多人。变蒸或早或晚,依时如法者少也。初变之时,或热甚者,违日数不歇,审计日数,必是变蒸,服黑散发汗。热不止者,服紫霜丸。小瘥便止,勿复服之。其变蒸之时,遇寒加之则寒热交争,腹痛矢娇,啼不止者,熨之则愈。变蒸与温壮、伤寒相似,若非变蒸,身热耳热尻亦热,此乃为他病,可为余治。审是变蒸,不得为余治。”
唐代孙思邈《千金方·少小婴孺方》对变蒸的临床表现及治疗基础上照录《诸病源候论》,但有所补充,对于要紧处再加说明。比如对目睛症状又云:“目白者重,赤黑者微。”“单变小微,兼蒸小剧。”“儿生三十二日一变,二十九日先期而热,便治之如法,至三十六七日蒸乃毕耳。恐不解之,故重说之。”对于治疗则更为谨慎,初变之时“有热微惊,慎不可治及灸刺,但和视之,若良久热不可已,少与紫丸微下,热歇便止。若于变蒸之中,加以时行温病,或非变蒸时而得时行者,其诊皆相似,惟耳及尻通热,口上无白泡耳。当先服黑散以发其汗,汗出温粉扑之,热当歇,便就瘥;若犹不除,乃与紫丸下之。”这样变蒸与时行的鉴别和治疗就更为明确了。
明代万全认为,其轻者不用治疗,重者根据症情施治,若夹杂他病则治他病,并认为古方黑子散姑可置之。他在《万氏家藏育婴秘诀·变蒸门》中说:“轻者不需服药,重者以平和饮子微表之。热甚便结,以紫霜丸微利之。若吐泻不乳多啼者,调气散治之。”又在《幼科发挥·变蒸》中说:“古方黑子散,姑置之可也。其间或有未及期而发热者,或有变过热留不除者,抑有他故,须详察之。如昏睡不乳,则不需治,待其自退。变蒸兼证:变蒸之时,有外感风寒者,宜发散,惺惺散主之,按摩法亦可用也:有内伤乳食者,宜须消导,胃苓丸主之;轻则节之可也;有被惊吓及客忤者,安神丸、至圣保命丹。如变蒸而后受病,以治病为主,慎勿犯其胃气。……如受病后而变蒸,以养正补脾为主,钱氏异功散加对病之药。”
明代鲁百嗣《婴童百问·变蒸》云:“变者易也,蒸于肝则目眩微赤,蒸于肺则嚏嗽毛耸,凡五脏六腑、筋脉骨节,皆循环各有证应。其治法,平和者微表之,实热者微利之,或不治亦自愈,可服紫霜丸一丸或二丸,并黑散子、柴胡汤。变蒸者,有寒无热,并吐泻不乳多啼者,当归散调气散主之。”
明代徐春圃《古今医统大全·变蒸》云:“但看何脏见候而调之为妙,如蒸于肝则目昏而微赤,蒸于肺则嚏咳而毛竖,蒸于脾则吐乳或泻,蒸于心则微惊而壮热,蒸于肾则尻冷而耳热,五脏六腑各见其候,以意消息调和,不必深固胶执而返求全之毁也。抑此自然有是变蒸之理,轻者不须用药,至期自愈,甚者过期不愈,按候调之,着中而已。”
明代龚廷贤对变蒸的治疗也是很慎重的。他在《万病回春·小儿初生杂病》中说:“凡变蒸不宜服药,或因伤食,因伤风,因惊吓等项夹杂相值而发,令人疑惑,亦须守候一二日,俟病势真的,是食则消食,是风则行痰,是惊则安神。若变蒸而妄投药饵,则为药引入各经,证遂难识,而且缠绵不脱,盖药有所误也。”
对变蒸的临床表现,明代方贤在《奇效良方·变蒸》中对头额上脉纹的变化作了细致观察。他认为:“观诸变蒸热作惊,须视日角左边眉间脉红是也。大凡初蒸见一条,长一二分,在眉上者轻,自日角垂至眉上者重。变蒸发热,见二条红者,两次蒸,热在内不解,脉红带叉;因惊而蒸,脉青。变蒸多次,青在左太阳,因伤风而蒸。自囟门青至眉之上,因惊而蒸。三处皆青,三证皆见。”(以上整理参见朱锦善《小儿变蒸学说的源流与学术争鸣》及佚名文章《试析小儿变蒸学说的科学内涵》)
五、变蒸之我见
古人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了小儿在出生后的一段生长发育时间内出现变蒸这一现象,并对变蒸时日和临床表现作了详细记录,虽然各自根据自己所见不同有不同的记录,但都来源于临床,我们不可以简单加以否定而摒弃。
古人没有阐明新出生小儿出现变蒸的原因,我们认为,变蒸出现的发热、汗出、烦躁、不欲食等现象,这是小儿出生后天与人结合时的反应,如同化学中两种物质结合时的反应那样。
由于小儿所带父母遗传物质以及出生后576天时段内的自然气候、环境不同——五运六气的变化,如同参加化学反应的物质不同,所以会出现不同的反应现象的不同记录,但异中有同。
关于这一点,陈复正在《幼幼集成》中指出与内在因素的禀赋及外在因素的营养、环境等有关,“婴儿之生,风土不侔,禀赋各异,时令有差,膏黎非一”。
《小儿病自疗法》的作者奚瓒黄也谓“气质变化之微必有因。比如四时代谢,四时必有寒热温凉、风雨晦暝之变纪,而小儿气质变化,神情上岂无一种现象?其乍寒乍热、精神不畅,或不乳吐哯等证,皆是气质变化表露于精神上之现象也。”揭示了形神生长发育的规律。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为其差异争论不休了。
至于变生脏腑,主要有二说:
一是钱乙等按天地生成数顺序来定脏腑生成顺序,为肾(一六数)→心(二七数)→肝(三八数)→肺(四九数)→脾(五十数)。这和《灵枢·卫气行》所叙卫气行阴的按五脏相克顺序肾→心→肺→肝→脾相仿,只是肝与肺的顺序颠倒了。
二是刘昉的变生脏腑次序,为肝→肺→心→脾→肾,按精神生长发育过程来定脏腑生成顺序。我们认为,既然天与人合于黄庭太极处,则宜先生土脾(经曰: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皆属于土),按五行相生的原则,则脾土生肺金(又《黄庭内景经·肺之章》说“肺之为气三焦起”。经曰:脾气散精,上输于肺。),次肺金生肾水(肺主气而统调水道),次肾水生肝木,次肝木生心火。至此血气藏心、神气舍心,而居帝位。所以《灵枢·天年》说:“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
朱丹溪《幼科全书》说:“万物生于春,长于夏者,以阳主生长也。于人亦然。所以变蒸足,始乃成人,血气充实、骨肉坚牢也。”这和《幼科发挥》所说婴儿从“一岁血肉”到“大小蒸毕,乃成人”,是一个道理,揭示了人体生命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规律。从其临床症状表现体热、耳冷、尻冷、上唇起白泡的特征来看,唇属脾,耳尻属肾而三焦统之,则与脾和三焦有关,这个反应当先起于黄庭太极,是为证明。
我们从“变蒸”一词也可以看出这一道理。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说:“变者,易也。”《周易》《内经》都解释为自然规律的变化。《幼科全书》说:“蒸者,蒸蒸然热也。”热乃心气也。既曰蒸,必有水火,火吹水腾之象也。故徐春圃《古今医统》说:“初生小儿变蒸者,阴阳水火变蒸于气血,而使形体成就。”